瀟湘河畔,千年零陵,這里有一所沒有“圍墻”的大學(xué)——永州電大,集學(xué)歷教育、干部在線教育、社區(qū)教育為一體,以“互聯(lián)網(wǎng)+”信息技術(shù)為支撐,以服務(wù)全民終身學(xué)習(xí)為己任。這里還有一群滋蘭樹慧、默默耕耘的電大人,以教為榮,以校為家,在他們當(dāng)中還有這樣一些“特殊”的老師,從祖輩相傳,堅(jiān)守講臺(tái),傳道授業(yè),書寫著平凡而有意義的教師世家故事。
播撒理想種子,延續(xù)教育薪火
過了一個(gè)暑假,蔣泓露仍然是黝黑的一張臉,脖頸處、胳膊上有明顯的分層。對(duì)此,他自己渾不在意。
今年六月下旬,永州電大開辦全市村(社區(qū))基層組織人才定向培養(yǎng)集中學(xué)習(xí)培訓(xùn)班,蔣泓露擔(dān)任教官,一個(gè)人負(fù)責(zé)八個(gè)班的軍訓(xùn),與兩百多名學(xué)生一起雨淋日曬。這樣的日子,他不覺得苦,只覺得暢快。讓他想起當(dāng)年在部隊(duì)當(dāng)兵時(shí)的生活,與戰(zhàn)友們同吃同住,一同摸爬滾打,建立起深厚的友情。如今,面對(duì)這群學(xué)生,他亦有著相同的感情。他覺得,學(xué)生就是他的戰(zhàn)友。談到自己的學(xué)生,他喜笑顏開,自信滿滿地說:“再給我?guī)讉€(gè)班,我也帶得下。”
作為曾經(jīng)的軍人,退伍后成為一名教師,對(duì)蔣泓露來說,不是偶爾,而是必然。爺爺蔣錫瑯二十五歲開始就在雙牌縣瀧泊鎮(zhèn)、永江、何家洞等邊遠(yuǎn)山區(qū)教書,那時(shí)的條件十分艱苦,待遇也十分低下。尤其是山區(qū)學(xué)校往往三、四個(gè)年級(jí)只有十來個(gè)學(xué)生,他一個(gè)人打包場,不辭辛苦,往返在家庭與學(xué)校之間十幾里的山路上,常年以校為家,以孩子為重。有的孩子太小,家長收工很晚,他還要走幾十里的夜路送孩子們回家,自己回來時(shí),只有漫天星斗與田間蛙鳴作伴。當(dāng)?shù)乩习傩斩挤Q他是“保姆老師”。蔣泓露的父親蔣淵民就是受自己父親的影響,八五年大學(xué)畢業(yè)即分配到雙牌黨校任教,扎根政治教育達(dá)三十余年,始終堅(jiān)守干部教育事業(yè)。從小,他就聽爺爺和父親念叨當(dāng)老師的好處,這些話在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一粒種子。退伍前夕,他腦海里反復(fù)想起爺爺在燈下備課、改作業(yè),父親在講臺(tái)上慷慨激昂講課的畫面。他明白了自己心底的向往,退伍安置工作時(shí),不假思索選擇了農(nóng)機(jī)學(xué)校,刻苦鉆研業(yè)務(wù),后因表現(xiàn)優(yōu)秀調(diào)至永州電大擔(dān)任教師,獲得過全市“優(yōu)秀運(yùn)動(dòng)員”、“優(yōu)秀共產(chǎn)黨員”、“優(yōu)秀工會(huì)積極分子”等多項(xiàng)榮譽(yù)。
既是緣分巧合,也是對(duì)教育事業(yè)熱愛的投射,蔣泓露的妻子黃仕芳也是一名教師,就職于永州職業(yè)技術(shù)學(xué)院醫(yī)學(xué)院。三代四人投身教育一線,如今夫妻二人正在逐步引導(dǎo)孩子,爭取讓下一代也可以投身教育,為新時(shí)代的教育事業(yè)出一份力。
師道傳,家風(fēng)延,澆灌滿園桃李
每當(dāng)學(xué)生叫“符老師”,符藍(lán)的內(nèi)心是平靜滿足的。這也讓她想起自己的爺爺和父親。這個(gè)稱呼不僅屬于她,也屬于他們。
符藍(lán)的爺爺符興明,是一個(gè)干干瘦瘦不起眼的老頭,很多時(shí)候還有些小啰嗦,不時(shí)叨叨。但是,在上個(gè)世紀(jì)五十年代,他是村里唯一考上湘西第二師范學(xué)校的“秀才”“高材生”。這所學(xué)校前身是抗日戰(zhàn)爭時(shí)期創(chuàng)辦的國立茶峒師范學(xué)校,根據(jù)抗戰(zhàn)形勢(shì)和湘西民族教育的需要而組建,在當(dāng)時(shí)吸引了許多老師、學(xué)子流離輾轉(zhuǎn)而來,開啟了湘黔川邊區(qū)教育先河。
爺爺作為當(dāng)年遠(yuǎn)近聞名的“秀才”“高材生”,畢業(yè)后直接分配在古丈縣委宣傳部任職。然而,工作之余,望著遠(yuǎn)山綠水、落日飛鳥,他總是時(shí)常想起學(xué)校那口用來提醒上下課的鐘。說是鐘,其實(shí)是一枚抗戰(zhàn)時(shí)期的炮彈彈頭,從學(xué)校成立之初,就立在那里,用它并不洪亮又有些悶啞的聲音,一聲聲提醒學(xué)子們“不忘國恥、奮發(fā)圖強(qiáng)”。這口鐘響過爺爺?shù)那髮W(xué)歲月,也響進(jìn)了他靈魂深處。當(dāng)時(shí)已然走出小山村的爺爺,總是隱隱聽到鐘聲回蕩,好像在提醒著自己——“我的學(xué)校是以培養(yǎng)師范生為使命的,我也應(yīng)當(dāng)以教書育人為使命,才不至于荒廢所學(xué)!”堅(jiān)定了想法,也為了追尋內(nèi)心真正的安寧,他辭去了縣城安穩(wěn)的工作,回到了家鄉(xiāng)小學(xué)執(zhí)教,開啟了自己余生如一日的教書生涯。
爺爺“舍棄萬千繁華守護(hù)一方凈土”的舉動(dòng),深深影響了父親符文貴。1992年,父親從湘西州農(nóng)業(yè)學(xué)校畢業(yè),回到爺爺最初任教的默戎鎮(zhèn),成為當(dāng)?shù)芈殬I(yè)中專學(xué)校的老師。那時(shí),他剛走出校門,還很年輕,學(xué)生們將他喚作“哥哥”,下課喜歡圍著他轉(zhuǎn),他也樂于跟學(xué)生打成一片,帶著他們辦活動(dòng)、搞實(shí)習(xí),忙得不亦樂乎。之后,了解到鄉(xiāng)下專任教師缺乏,他主動(dòng)申請(qǐng)調(diào)到坪壩鄉(xiāng)中學(xué)當(dāng)老師,教過物理、生物、化學(xué)、語文、數(shù)學(xué)、音樂等各科各目,可謂“萬金油”。忙碌之余,他不忘提升自己,參加湖南師范大學(xué)漢語言文學(xué)專業(yè)的自考。他白天教課,晚上守自習(xí)、查完寢,回到家中攤開書本繼續(xù)學(xué)習(xí)。他孜孜不倦的立學(xué)之道,在學(xué)生們心里種下了奮發(fā)讀書的種子,數(shù)不清的孩子或考上了心儀的大學(xué),或?qū)W得一技之長,一步步走好人生之路。后來,他調(diào)入古丈縣委黨校繼續(xù)授課。從教近三十年,雖然授課的地點(diǎn)在變,授課的對(duì)象在變,但不變的是那顆教書育人的初心。
如今,符藍(lán)也帶著這份初心在永州電大開啟了自己的教師生涯。她期待著,以自己的努力育桃李,有朝一日收獲滿園芬芳。
賡續(xù)百年初心,擔(dān)當(dāng)育人使命
永州電大人當(dāng)中,除了一家三代都是老師的蔣泓露、符藍(lán)家庭,還有三代五位教師的顧明家庭,更有溯源到十九世紀(jì)中期的六代教師世家唐臻滿家庭......
他們,從祖父輩手中接過的不僅僅是一根教鞭,傳承的不僅僅是一份職業(yè),更是一種家風(fēng),一種精神。他們,與所有電大人一道,帶著對(duì)教育的愛與熱情,滿心投入到學(xué)校轉(zhuǎn)型提質(zhì)的發(fā)展中來,投身到構(gòu)建永州終身教育體系、建設(shè)學(xué)習(xí)型社會(huì)的事業(yè)中來!
40年弦歌不絕,逐夢(mèng)前行。有這樣一群人的永州電大,明天會(huì)更好!(永州電大 顧明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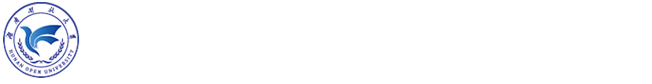

 湘公網(wǎng)安備 43010302000938號(hào)
湘公網(wǎng)安備 43010302000938號(hào)